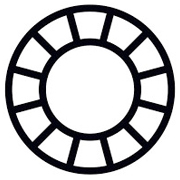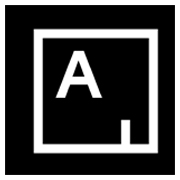马秋莎通过发现与整理她外祖父(一位传统戏剧演员)的遗物重访这位亲人的人生时,逐渐打捞出一个远比其想象中更为陌生的亲人形象。正于蔡锦空间展出的马秋莎个人项目“一个青年”围绕着这段对于时代与生命的轨迹的重访展开,在纪实与想象(人或人机的)的交错中,两位“创作者”之间的距离不断变化,重叠又分离,延续着艺术家有关历史与个人,记忆与想象,亲密与隔阂的探索。
“早在2011年,我有一件名为《比我小两岁》的作品,在当年的自述中我写到:“我的姥爷是唯一一个’不溺爱’隔代孩子、和我吵过架的老人。后来听我姥姥说姥爷和我一样,也是独生子。他确实很‘怪’。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他反常且认真的行为——把每次刮下来的胡茬儿都装进一个小药瓶里然后锁进抽屉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 去年他走了,在一堆被扔掉的物品中我拣回了这些小药瓶。从1984年开始,他每年用一个药瓶存放当年的胡茬儿, 数数共27瓶,正好比我小两岁。”(由此得名《比我小两岁》) 当时它在UCCA的个展《地址簿》展出之后就一直存放在仓库里。
2020年初的一天,我困在家中不能出门。那是一个平常的午后,阳光被云遮着,屋里时明时暗。我正坐在电脑前浏览着网页。就在一个页面跳出的刹那,一张老照片映入视网膜—— 那是一副画过妆的男青年的脸庞。
就在那一刻他再次与我相遇了。
确切的说这是一张双人肖像,是前苏联摄影师弗拉季斯拉夫·米科沙Vladislav Mikosha于1950年5月4日在北京为庆祝建国后第一次青年节活动上拍摄的照片。在这张照片中,右侧男青年的相貌酷似年轻时候的姥爷。随后我从家人那里得知,1950年春夏之际他正备考中央戏剧学院的舞台表演专业,确是在北京无疑。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姥爷。
有什么东西又被翻腾出来,仿佛似曾相识,却又似是而非。
我无数次地端详照片中的脸,在特征重叠的五官里我却不能与姥爷联系起一丝一毫。
我从新翻开他的相册。大大小小的英雄形象笼罩住他的身体。在那里,他是陆游,是岳飞,是邓世昌;他也是矿工鲁大海、是烈士许云峰、是班长王德均;他还是车间主任丁海宽、是农村工作部部长孟莳荆、是工程师顾成林;他甚至是外国人,是列宁、是日丹涅克、是穆卡尼亚、是契科夫……他仿佛无处不在,无所不是。在那里,他可以是任何人,却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
我打开封存着他遗物的箱子,几乎被稿纸填满。我小心翼翼的展开这些蝉翼上的叙说,就像进行着一场触目惊心的手术,它们脆弱的载体正在消逝。我被他暮年时写的自传式回忆录深深地吸引。回忆对他来说是如此艰难,它们支离破碎有始无终,是在夜深人静时才敢发出的声响。在这里,我所有与他有关的记忆就像一场做了很久的梦,亦或是一场持续了很久的幻觉,也许我从来就不曾真的见过他。
我试着将近百篇断续的讲述拼接成一个整体,一个名为马超的年轻人渐渐浮现在面前。他是一个挣扎在随波逐流里的人、是一个不断遭遇失败的人,是一个充满细节的人。这也是一位艺术家对自己前半生的回望,更是他生命的密码。以1950年5月4日为时间节点,那时他二十三岁,正值青春年华。”
(⻢秋莎 2025 4 北京)